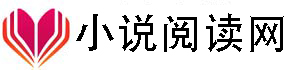20-26(8/17)
咬下去。下一秒,陈亦扬突然从身后抓住她后腰,不容拒绝将苗荼整个人掰过去,然后攥着她手腕就往旁边拽。
事发以来,这是苗荼第一次剧烈反抗,喉咙不断发出尖锐又嘶哑的声音。
余光里,学生们推门一个个进去,记者被迫留在外面,只恨不能将镜头和收音设备伸进会堂,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、说的每句话都逐一记录,好刊登在明天的头条位置,又是一条爆款。
苗荼不顾一切甩开手,几乎是一巴掌正好甩在陈亦扬脸上,打得她掌心发麻。
陈亦扬硬生生挨了打,还是紧紧攥着她胳膊,再次露出乞求表情,开口即落泪:“别这样。”
“求你了,别这样。”
“凭什么。”
苗荼喉咙干涩,像是有人在用尖刀刮磨着她的声带;她眼眶通红却绝不肯落泪,含糊不清地再次重复:“凭什么呢。”
外面那些自称“徐砚白同窗”的年轻学生,穿着她高攀不起的昂贵衣服;他们才刚经历过高考,正值青春最美好的那一年、人生拥有无限可能。
往后人生,这些人可能会读研究生或工作创业,可能会结婚生子或保持单身,可能会经历最精彩的成功、或者最庸俗的失败。
但所有这一切的喜怒哀乐,徐砚白全都体会不到了。
那个永远对世界抱有善念的男生,长眠于十八岁的前一日,被离岸流带往海底深处,尸骨难寻。
他究竟做错什么了,凭什么是他呢。
凭什么是徐砚白的脊柱一寸寸被压弯、灵魂一点点被扼杀,而曾经口出恶言、谣谣相传的人,只是用轻飘飘的一句“没有恶意”,就可以假装一切都没发生、转身就去过各自的人生呢?
那些不明真相的恶言相向、那数不清的相机与话筒,才是真正的杀人犯,不是吗。
这么多天过去,苗荼始终想不通其中道理;
以至于她还没真正接触社会,就已然对这个世界有了许多无能为力的悲愤-
葬礼三天后,苗荼接受了人工耳蜗手术。
手术意料之中的很成功,一个半小时后,苗荼被推出手术室,耳后多了道切口伤疤,在头骨耳后向上的地方埋了片薄薄的耳蜗接收器。
耳蜗使用时间因人而异,有人拆线当天就开机,也有医生考虑到年幼的孩子发育、保险起见等到一个月后再开机。
得之自己术后状态恢复良好,苗荼坚持要在拆线当天、也就是术后第七天开机。
按照约定,陈律师来医院见她时,会带上徐砚白留给她的部分个人物品:一封信、一根录音笔、一块橡皮擦、以及那把他随身携带的小提琴。
徐砚白生前积累了相当的财富,即便按他所说、要先赔偿父亲的损失,剩余分给苗荼的数目依旧十分可观。
徐家父母对儿子的财产分配极不满意,正在准备打官司,陈律师几次找到苗荼,希望她本人能积极参与进来。
苗荼却只是催他,能不能快点将那封信和录音笔带过来。
陈律师无奈之下,只能约定两人在苗荼拆线当天见面,他会如约带着最不值钱的信和录音笔来到医院。
拆线时,苗荼双眼紧盯门外,整个人坐立难安,焦躁模样连护士都忍不住笑道:“别紧张,我拆完线就给你开机,一点点适应就好了。”
苗荼在座位上心不在焉地点点头,直到门口玻璃出现熟悉人影,她在护士惊呼声中蹭的起立,将开门进来的陈律师吓了一跳。
六月中旬酷暑难耐,午时烈日打在身上同蒸拿房没甚区别,陈律师进门后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