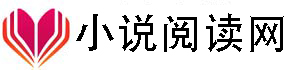20-26(7/17)
尽眼底,心猛地下沉——绝不是错觉,他这几天越来越频繁地在苗荼身上,隐约见到曾经徐砚白的影子。在陈兰萍眼神示意下,陈亦扬拉着苗荼去了走廊尽头,憋了半天沉声:“毕竟是他父母,别在他面前这样。”
苗荼其实很想说,徐砚白人都没找到,又何谈“面前”,但她不想争辩,乖顺地点点头。
她直勾勾望着窗外参天大树,想着这一棵和徐砚白总看的百年梧桐有什么区别,不知过了多久,旁边的陈亦扬拽她衣袖,扭头朝向紧闭的灵堂大门,问她要不要进去看看。
脚底感受到震动,苗荼猜应是灵堂内正播放哀乐,摇头拒绝。
她早就过了偷吃贡品的年级。
况且,徐砚白也并不在那里。
陈亦扬拿她没办法,低着头,双手抱胸默默陪在苗荼身边,靠墙听着悲戚的奏乐声从灵堂内钻出来,嘴角紧绷。
兄妹俩相对无声地收到走廊外,直到乐声渐止,对面门外却传来嘈杂的闷闷脚步声,夹杂着低沉的窃窃私语。
殡仪馆被徐家租下一整天,按理说不该出现混乱场面。
陈亦扬皱眉抬头向声源处看去,却发现身旁的苗荼早已冲出去、直奔灵堂门口,速度快到他甚至来不及抓住她手腕。
不知何时,原本空寂凄凉的门口站满了人,最前面约莫三四十名都是学生模样,约莫十七八岁穿着黑色衣服、胸前别着白色花朵。
而在学生身后的,是乌泱泱一群手持炮筒式摄像机、疯狂将话筒和收音麦往前递的记者。
陈亦扬目光落在最前面的男生身上,认出对方是被他迎面打过一拳的蒋臻,漆黑的眼里染上怒色。
他攥紧拳头准备上前,却猛地发现乌泱泱的人群忽地停下脚步,齐齐望着用瘦小身体挡在门前、不许任何人进去的女生。
苗荼全然看不清楚,眼前的人都在七嘴八舌说些什么。
“我们是徐砚白的同班同学,想来送他最后一程。”
“当时我们只是吓坏了、才说了不好的话,没有恶意,也没想到会是现在的结果。”
“我们进去吊唁也不行?还有你是谁啊?”
“神经病吧,凭什么当在这里啊?”
“”
对听障人士而言,最大侮辱也不过是在她面前快速的、疯狂不停的说话,苗荼眼睁睁看着这些人失去耐心,甚至有几个心急的男生几次想冲上前,眼神警告她滚远点。
闪光灯噼里啪啦闪个不停,漆黑镜头像是吸人魂魄的黑洞,收音设备宛若沼泽地里生出的藤蔓,一条又一条伸向她;苗荼被光线刺的睁不开眼睛,后背死死抵在冰冷的灵堂大门。
毫无征兆的,她想起那天晚上,第一次在网上搜索徐砚白。
在数十台相机瞄准中、在数不清的话筒收音麦、在所有人厌恶与不齿的眼神中,徐砚白也曾反反复复鞠躬道歉,直到胸背再也无能挺直。
在这一刻,苗荼倏地识到,她被父母和兄长保护的多好,才能一直安然在象牙塔里平安快乐的长大。
可她现在除了拦在门前,还能如何对抗来自这个世界的恶意呢?
她是个聋子、连别人骂她都听不见;她也不会说话,连别人唾弃她都不会还嘴。
她不是徐砚白的任何人,今天没凭没据地站在这里,甚至都是别人的慷慨允许。
那她还能为徐砚白再做些什么呢?
苗荼瞪着眼睛、不许任何人靠近,直到终于有人不耐烦上前,试图抓住她肩膀甩走。
她躲都不躲,下意识就要低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