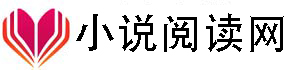20-26(10/17)
白录音,知道哪里是开机与播放键,手抖的摁了三次才启动播放。“”
耳边响起滋滋啦啦的声音,杂乱无章。
苗荼根本听不到人声,看着小屏显示的【1/1611】,切换到下一条。
滋滋啦啦。
眼底闪过一丝错乱,她将录音笔贴在耳边,再次切换到下一条。
滋滋啦啦。
在陈律师欲言又止的复杂神情中,苗荼接连换了几十条,耳边永远都只有滋滋啦啦的杂音,除此之外,再没有任何声响。
她终于有些慌了,怕冷似的牙齿开始细细打颤,小屏前半部分数字从个位数切换到大三位数,嘈杂的滋啦声也分毫未变。
陈律师实在不忍心,出声打断:“录音笔被海水侵蚀的太严重,几乎所有文件的损毁了。”
苗荼置若罔闻,只是牙齿打颤的更厉害,直到她以为自己下一秒就晕过去时,耳边终于响起一道陌生的温生男声。
“苗荼。”
苗荼心脏猛地一颤。
时隔八个月,她第一次听见徐砚白的声音。
男生声线沉静温润好似山涧清泉,念起她姓名时,尾音会不自觉上扬拖长,无端带着些缱绻与纵容的温柔轻笑。
当苗荼屏息等待下文时,令人绝望的滋啦声再度响起,无论她怎么反复倒回又重听,永远都只有徐砚白喊她姓名这两个字。
这一刻,苗荼感到前所未有的慌乱与惶恐——甚至在得知徐砚白死讯时,她更多都只是茫然无措。
如溺水者在汹涌浪涛中找到浮木,苗荼在慌乱之中,死死抓住身边陈亦扬的袖子,喉咙里发出不知是尖叫、还是哭泣的呜呜泣声。
眼眶湿润,眼前景象在泪水中剧烈晃动,苗荼看见陈亦扬在她面前蹲下、看见所有人都着急围上来,焦急问她发生什么事了。
她宛如牙牙学语的婴儿,无助地咿咿呀呀抓着手里的录音笔,用力地胡乱戳着自己的耳朵,用破碎的手语一遍又一遍问:
【哥,我是不是耳朵没好啊?】
【为什么,我什么都听不见呢。】
徐砚白明明在信里写过,说他还留了很多话给她的。
为什么她什么都听不见啊。
苗荼从来不是会哭的孩子。
小时候摔倒受伤不哭,耳朵聋了她不哭,被人欺负聋哑也不哭,甚至在被迫接受徐砚白死亡的真相时,她都从没掉过一滴眼泪。
不是不委屈、不是不难过,是苗荼清楚如果她落泪,总有人会比她更难受、更自责、更耿耿于怀。
她总想着,再忍忍吧。
再忍忍就会过去的。
而在当下这一刻,在意识到徐砚白留给她最后的念想也被彻底断送时,她终于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第26章 我怎么舍得让你一个人。
离开上海之前, 苗荼去了趟南汇新城海滩。
七月盛夏酷暑难耐,拂面而过的风都像热卷席而过,正是退潮时间, 大片淤泥裸露。
人影绰绰,自发前来的人们手捧鲜花,面露悲戚,弯腰将花束放下, 停顿片刻不知是悼念或惋叹,转身离开。
苗荼看着木槿与白菊开满整片海滩, 莫名想起故乡郦镇漫山遍野的荼靡,妍艳、绮丽、争相绽放。
天不亮时,她搭乘最早一班公交来到海边,带着皱巴巴的告白信和高考录取通知书。
兄妹俩双双高考超常发挥,陈亦扬一举拿下全省第六、如愿考取清华,而苗荼也第一次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