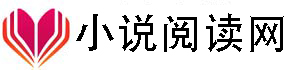20-26(15/17)
热泪盈眶的幸福。她拿起相机拍照,看着眼前年龄同他相仿的一对新人,心中一片柔软。
口袋手机响铃,是助理的电话。
“苗老师,米秀杂志的采访,您真的不考虑吗?这可是国内顶级时尚周刊,第一次给年轻女纪录片导演的专访,更何况还是头版呢。”
太阳当头有些刺眼,苗荼站到阴影下,轻笑:“让我猜猜,是不是有关‘无尽夏’的专访?”
如她所料,对面果然陷入沉默。
说来不知是苗荼幸运还是悲哀,她本科毕业后没有从事新闻相关工作,反而一头扎进纪录片拍摄,三年后带着处女座《无尽夏》,一举斩获最佳长篇纪录片、最佳新人奖、最佳编导等各类奖项。
凭着这部作品,她一个新人在业界名声鹊起,主动找来的团队和投资方数不胜数;也同样是这部作品,让苗荼至今再难超越,不止一次被业界锐评“灵气折损”,大有埋头苦干数十年,归来是一部“无尽夏”。
苗荼对此并无芥蒂,对她而言,作品只是映射她人生一段路程,拍完即过,获奖与否、外加评价并不太重要。
她只是不想,再过度消费《无尽夏》这部作品——以那个夭折在18岁前夕的天才小提琴为主角的纪录片。
苗荼低头摆正左手腕的蓝色发圈,温声拒绝:“相关采访我接受很多了,能说的都说过,也没什么人想再看了。”
“怎么会!”助理立刻反驳,“不说别人,单单说我都想好奇,徐砚白在最后那片花海里,究竟说了什么?”
苗荼坦言: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您怎么会不知道呢?!”
不同于通常纪录片客观的第三视角,《无尽夏》时常会出现主观色彩极强的第一视角镜头,比起记录主人公的一生,更像是透过一个人的眼睛,去看她/他眼中的主人公。
其中最经典的镜头,是临近片尾时,男生分明是独身一人寻到山上荼靡花海,始终站在花海之外,最后忽地微微笑起来,只露出半张侧脸,却能清楚看到他在说话。
作品问世后,有关“徐砚白那日在花海中究竟说了什么”的相关话题热度高居不下,连苗荼也被问到数十次。
起初她总是笑笑,如实回答:“他说,‘一起回家吧’。”
后来发现没人相信,索性就用一句“我也不知道”,一笔带过。
好比现在。
苗荼无奈重复: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时间过去太久,其中细节早就模糊,她只记得自己身处花海,直觉17岁少年同她说话,于是回头询问。
永远年轻的少年站在花海之外,笑容温和:“时间不早了,一起回家吧。”
至于他之前说了什么、到底有没有说话,苗荼全然想不起来。
挂断电话,苗荼收起手机折回教堂,见那对新人从正门出来。
此时有风吹过,扬起美丽新娘的头纱,飘飘扬带到空中,最终留挂在教堂塔尖。
苗荼心中微动,举起相机记录,久久望着头纱随风飘动。
仪式结束后,她找到那对新人夫妻,将拍摄的几组照片给两人看,算作新婚祝福。
看过照片后,名叫“盛穗”的新娘红了眼眶,不好意思地用手轻拭眼角,感激道:“这是我的丈夫,周时予;请问,您手上的照片可以发我一份吗。”
苗荼笑着答应。
启动蓝牙功能传送,苗荼看着相机屏幕里亲吻的两人,再次为之动容。
得知两人相识年少,周时予默默守侯盛穗、历尽万难才换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