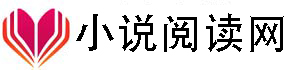14-20(22/29)
他低头编辑短信,敲字时指尖仍轻轻颤着:【你现在方便打电话吗?】【我想听听你的声音。】
【哪怕只是呼吸声也好。】
第19章 我很想你。
电话很快打过来。
“徐砚白。”
漆黑房间, 听筒里传来女生清亮声音,仿佛炎热夏季的一捧山泉,模糊不清, 但听得出每个字都努力咬的很重。
通话随即陷入沉默。
徐砚白嗯了一声,点开免提耐心等待,直到掌心手机再次震动。
【苗荼:我不太会说话,还是打字吧。】
像是难为情, 扬声器有很轻的鼻子抽动声响起。
徐砚白抬眸望向对窗,看见刚才端正坐好的女生, 此时正侧趴在书桌前,柔顺的长发披散着。
他回信宽慰:“已经说的很好了。”
徐砚白对聋哑人了解不多,只知道大多数人失去听力后、语言功能也会逐渐丧失。
陈亦扬说过,苗荼是11岁高烧时,滥用抗生素导致的药物性耳聋,在这之前一直是能听、能说话的健全儿童。
被问起为什么不佩戴助听器时, 陈亦扬的解释是, 普通助听器的最大输出无法达到苗荼的听力阈值, 只有进行人工耳蜗手术,才有可能恢复部分听力。
不说高昂的手术和后续康复训练费用,光是最普通的国产人工耳蜗, 都要五万元一个。
以苗荼的家庭条件,这是一笔倾家荡产也难以承担的费用。
徐砚白原以为,苗荼会像陈亦扬所说的,完全失去说话能力;直到跨年夜在山坡上, 女生踮脚凑到他耳边, 那句不甚清楚、但足够完整的感谢。
苗荼是能够、或是一定想要说话的。
徐砚白询问:“你有想过,以后开口说话交流吗。”
【苗荼:我查过, 上海有不少聋哑人的互助小组,有很多在小组帮助下、聋哑人重新开口的例子。】
【苗荼:如果能去上海读书,我想试试。】
似乎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,苗荼换了个话题:【过两天就是除夕过年,你要留下来陪徐奶奶吗?】
徐砚白垂眼沉默,指尖犹豫在屏幕敲字:【我要回去一趟,有事要处理。】
苗荼过了一会才回复:【过年是要回去的,毕竟家人都在那边。】
再正常不过的内容,徐砚白却在字里行间读出点委屈,他打字想解释,苗荼先提出要学习,没有挂断电话。
徐砚白回了个“好”。
戴上耳机,徐砚白右手撑着太阳穴,目不转睛的看着窗帘后的女生拿出试卷与书本,半伏在桌面学习。
一时间,耳边只剩下试卷翻动声、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、以及女生的清浅呼吸声。
二楼那盏灯彻夜亮着,各一端的两人都闭口不提未挂断的电话,默契地保持沉默。
直到徐砚白在悠长平稳的呼吸声感受到困意袭来,入睡前,很轻地说了句“晚安”。
一夜无梦-
除夕当日,徐砚白坐飞机返回上海。
不想引人注目,他没将琴盒带在身边,独自搭乘最早一班航班,与午时抵达生养他十几年的城市。
上海气候比郦镇温暖,徐砚白戴着口罩与鸭舌帽,下飞机后一路走过贵宾通道,感觉到闷热。
专车早早在出口等候,见徐砚白远远走来,徐家司机快步应上前,为他拉开车门。
黑色迈巴赫在柏油路面行驶,车窗外的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