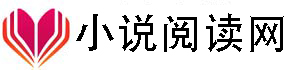20、灵山(2/40)
于公的私产清点完毕,与五年来王攀为朝廷赚取的矿税,对不上账了。是为何意呢?
王攀身为矿监税使,在江浙运作五年,明账上为圣上内库搜刮了价值数以百万两的矿税,可谓一大功臣。
可既是功臣,便要顶住骂名办事;想好办好事,手里便少不了用钱之处。
更何况,天下何曾有空甩鞭子、不给粮草,还盼着马儿日行千里的道理,在这个位置上,矿监税使“适当”地吞些好处,皇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也就过去了。
其中份额多少、数目多少,虽不曾摆在明面上讲,可彼此心中都有数。
可坏就坏在,王攀那即便清点后已是车载斗量的私产,跟皇帝心里的“数”比起来,仍是九牛一毛。
那么问题就来了,王攀的大半私产,去了何处?
太监是皇帝的人,太监的钱,可不就是皇帝的钱么?
是谁又胆大包天,敢往皇帝的口袋里打主意?
圣上在京震怒,远在杭州的沈不器便接到密信,要他继续查清,王攀在浙江经营多年的钱财,究竟去向何处。
甚至他原本不过一年的任期,也因为这特殊的案子,被无限期拉长——何时查清了,何时再回京叙职。
沈不器盯着那信半晌,心里只吐出一句:荒唐。
虽说幸得天家青睐,本是天大的喜事,可沈不器一想到,自己还有数个州府没有巡视按察,堆在桌上的案卷浩如云海;
外头各大小官员、远亲近邻,眼看沈不器前程大好,又尚未婚配,纷纷送来拜帖,想要与之结交;
眼下居然还得了急令,要暗中搜查王攀的财产去向……
沈不器一忍再忍,才没有破口大骂。
他有时真想不通,自己究竟是来当察吏安民的巡按,还是来当内库的账房先生了?
沈不器接到信后,一连烦躁了数日,至今仍未排解开来。
偏偏这差事还需秘密进行,沈不器满心烦闷,却无处诉说。
而林承宗亦不晓他满腹心思,只看见自家外甥将差事办得如此漂亮,很是与有荣焉,干脆拎着自己在家做的酒肉,喜滋滋跑来杭州贺喜。
可一见面,他就发觉不对——瞧他神情郁郁、寡言少语的模样,哪里有得胜将军的气派?
偏偏他职责特殊,许多话难以言说,林承宗只能干巴巴安慰几句,夜里思来想去,猜到个皮毛:
定是名声所累,耽误他正经办案了。
故而第二日临走时,舅甥俩顶着乌青的眼圈对望,林承宗半天憋出一句法子:
“杭州的事,不行就先放放。换个地方,微服暗访去。”
沈不器思来想去,也没别的法子,便应了下来。他这厢刚点头,林承宗回到绍兴家中,立马吩咐林锦程收拾包袱、陪表弟微服私访去。
三人这才结成一路,往远离杭州的衢州府去。
船一路西行,眼下刚出杭州,正行在桐江之上。
林锦程与冯乐之天南地北闲聊片刻,雨势渐大,便只能悻悻回到船舱之中。
冯乐之宿醉头疼,又回去睡回笼觉,林锦程则步子一转,到了沈不器屋前。
他意思意思敲两下门,不等里头应声,直接推门而入,只见屋中舷窗大开,疾风裹着骤雨卷进船舱,而沈不器身着简朴麻衣,在榻上闭目打坐。
他对窗而坐,碎发随风轻扬,身上素色的袖笼也被吹得鼓起。
假若不看他清俊出尘的容貌,单看身形姿态,再配着这满屋的藤席、麻垫,当真好似老